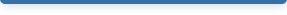程巍����,1966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岳陽市��,先后畢業(yè)于武漢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博士����,長期致力于英美文學文化史、當代西方(主要是法蘭克福學派和其他左派)文化理論和中外文學—文化關(guān)系史研究�����。其研究視野廣闊�,學術(shù)成果豐碩,代表作有《中產(chǎn)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lǐng)導權(quán)》《文學的政治底稿:英美文學史論集》《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種族主義想象力》《否定性思維:馬爾庫塞思想研究》《夏洛蒂·勃朗特:鴉片�����、“東方”與1851年倫敦博覽會》《語言等級與清末民初的“漢字革命”》等。這些著作不僅在學術(shù)界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也為理解和反思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9月20日,經(jīng)提名�����、資格審查����、學部評審、院外學術(shù)評鑒��、公示�����、學部委員選舉大會選舉��、院黨組批準�����,我院新增9名學部委員,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程巍是其中之一�����。近日����,本報記者對程巍進行了專訪����,在探尋其學術(shù)成長之路的同時,帶領(lǐng)讀者一同深入了解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現(xiàn)狀及未來發(fā)展���。
把興趣愛好變成一生志業(yè)
《中國社會科學報》:首先��,恭喜您當選我院學部委員�����。我們想知道���,您是在何種機緣下投身外國文學領(lǐng)域的?
程?。何业臄?shù)學能力并不出眾���,甚至有時會忘記自己的手機號碼,同時我對科技也抱有一定的恐懼感�����。因此���,我似乎只剩下投身文學這一條道路了�����?����;蛟S是因為受母親的影響�����,我從小就喜歡文學��,家里所藏的中外文學作品和文學刊物也不少�����。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文學的時代�����,作家和詩人的名望很高����,我身邊的不少小朋友都在寫詩。我讀的較多的是外國名著的中譯本��,也許由于俄蘇形式主義所說的外國文學之于本國文學的“陌生化效果”�����,讀起來覺得印象特別深刻���。至于高考時選擇中文還是外文,當初并沒有認真思考過�����,但后來報考了外文����。在武漢大學外文系的本科四年和北京大學碩士三年��,我的閱讀量很大��,也非常廣泛�,并漸漸明確以外國文學為自己今后的學術(shù)根據(jù)地�����,不僅學科的延伸性較好�����,還能獲得另一雙“眼睛”�。1988年我從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碩士畢業(yè),進入我院外文所外國文學理論室工作�。起初,我主要研究西方當代文學文化理論方向����,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后來轉(zhuǎn)向英美文學文化史研究方向���,再后來就轉(zhuǎn)向了全球史中的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文化史方向和中外文學文化關(guān)系史研究��。我很幸運���,一直在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興趣沒有轉(zhuǎn)移���,只是在不同的領(lǐng)域中擴展和延伸���,形成了新的分支。
《中國社會科學報》:了解您的人都知道�,您從大學時代就發(fā)表過不少小說作品。小說為您的科研帶來了哪些靈感��?
程?���。何倚W就開始寫詩���,還獲得過征文禮物����。但后來發(fā)現(xiàn)�,或者說承認自己不擅長韻律�,而擅長敘事�。于是,初中階段我就轉(zhuǎn)向了小說創(chuàng)作�,后被高考前的復習中斷。上大學后����,時間比較自由,但讀得多寫得少����。從研究生時期起,我在《十月》《收獲》《大家》等著名文學期刊上陸續(xù)發(fā)表中短篇小說���。不過�,十多年后�,我回看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覺得無非是在模仿�����,既沒有屬于自己的題材�����,也缺乏自己的寫作風格,多亦無用���,不如不寫����,由此擱筆了十幾年�,專心于學術(shù)研究。近兩三年�,我似乎突然找到了自己的題材和風格,就用零零星星的時間開始創(chuàng)作了����。我很注重小說的敘事方式,這一點對我的學術(shù)研究頗有影響����,因為我主要從事的是文學—文化史研究,而歷史(包括文學—文化史)也是一種敘事��;第三人稱的歷史敘事往往掩蓋了自己的敘事者�,因此也就掩蓋了“誰在敘事�、為何敘事、如何敘事”,但當你意識到歷史是一種敘事時�,就會體會到歷史敘事也是一種文學“制作”,后面晃動著受制于特定語境和特定意識形態(tài)的制作人��。
有人說文學創(chuàng)作與學術(shù)研究是難以合一的兩途����,其實不然。實際上����,外文所就有這么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學術(shù)研究”的傳統(tǒng),如馮至��、李健吾����、卞之琳、曹葆華���、楊絳�����、宗璞���、童道明�����、陳眾議�、陳樹才����、高興、戴濰娜等學者都遵循了這一傳統(tǒng)���。
《中國社會科學報》:1991年您就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至今已有30余年。在您的科研生活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故事?
程?��。何疫M外文所工作時25歲���,與外文所的學術(shù)氛圍和審美趣味不謀而合。當時��,外文所老一輩學者尚在���,還有比他們稍晚一輩的中年學者�����。他們身上大多具有一種灑脫不俗的氣質(zhì)�����,大家常常聚在一起高談闊論����,談的主要就是文學和翻譯���,也喜歡品評人物�����。到現(xiàn)在�,我在外文所已30多年��,印象深刻的故事自然很多。例如�����,當時理論室的主任郭宏安先生����,既是著名翻譯家,又是隨筆作家����。有一次,我想是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個夏天�,我隨他去長沙開會,坐的是60公里時速的綠皮火車��,路上走了近20個小時���,他一路跟我大談“隨筆之美”���。到長沙后,是凌晨四點��,無人接站���,我和他就坐在車站正面五一路的馬路邊上�����,一邊等待著天亮����,一邊繼續(xù)談“隨筆之美”:他一直主張慎用“四字成語”����,因為既然是成語,就必定帶有某種程度的俗套���,不能窮形盡相地描繪自己眼前的事物��。對自己的寫作和翻譯��,他以“煉字”要求自己�。郭宏安先生是法國文學研究專家��,一輩子在與兩種文字的糾纏中發(fā)展出自己的風格��。
想起自己曾經(jīng)交往卻已去世的外文所的老一輩和我的老師輩中的一些人����,我有時有一種蘭姆式的感懷��。例如�,童道明老師在退休后有時回到外文所�,坐在椅子上,周圍一圈本所的年輕人����,朗讀自己劇本的片段,他那種癡迷的神情��,讓人動容�����。外文所的一個可愛的風氣是“沒大沒小”�。的確,當你天天面對各國偉大的作品�����,當你在身邊見慣了學界名流的謙遜和風趣���,就會領(lǐng)悟到�����,在浩瀚的知識海洋和璀璨的人類智慧面前���,我們每個人都不過是滄海一粟�����。
致力于外國文學學科長遠發(fā)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目前外國文學學科發(fā)展現(xiàn)狀如何��?具體到外文所來說�����,為推進學科發(fā)展做了哪些工作����?
程巍:當今���,外國文學學科正在無私地為別的學科大量培養(yǎng)語言人才��,而使自身學科日益變得荒蕪���。文學情懷似乎早已凋零�,甚至在整個外國文學學科內(nèi)皆是如此��?����;蛘哒f�����,外國文學學科目前處在一種劇烈的“格局”變化之中�。一方面,學科界限被大大拓展�,另一方面,文學根據(jù)地正在日蹙百里�����。
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其實都是與“話語”的糾纏���,而話語的敏感性實質(zhì)就是文學的敏感性?�,F(xiàn)在我們屢屢談到政治敏感性����,但如果文學敏感性不足,又何談政治敏感性���?
外文所執(zhí)著于“以語言���、文學為主體,向翻譯學���,國別與區(qū)域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領(lǐng)域拓展”,并以此為宗旨����,同時結(jié)合國家的需要,對自身的研究室進行了重新調(diào)整���,力爭從“單一語種�、單一國家�����、單一方法”的研究室格局走向“多語種、區(qū)域化��、多學科”的新研究室格局���。
經(jīng)調(diào)整�����,外文所現(xiàn)有八個研究室���,從名稱上就可看出它們各自從事的領(lǐng)域:英美文學研究室更名為“英語文學研究室”,以容納更多的英語國家和地區(qū)�����;俄羅斯文學研究室更名為“斯拉夫文學研究室”�����,以容納包括俄羅斯在內(nèi)的三個斯拉夫地區(qū)��;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室更名為“外國文藝理論研究室”����,因為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研究是可普遍運用的方法�����,而非一個領(lǐng)域���,以研究領(lǐng)域立室才更為合理。從東方文學研究室分離出“梵文與南亞文學研究室”�,中北歐—古希臘羅馬文學研究室分為“中北歐文學研究室”與“古典學研究室”;中南歐拉美文學研究室暫時保持不變�,待人才儲備已足條件成熟,再考慮從中南歐拉美文學研究室分出“西班牙葡萄牙語文學研究室”���。
從外文所近十幾年展開的一些集體研究項目或重點學科來說��,體現(xiàn)了一種“有組織的科研”�,主要有“外國文學學術(shù)史研究”���,主要梳理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史;“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文學研究”��,服務于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文學與大國興衰研究”�����,研究語言文學之于歐美各國興衰的關(guān)系���;“中外文學關(guān)系史研究”��,從全球史視角來研究近現(xiàn)代中外文學及文化關(guān)系�����;“梵文研究”“古典學研究”以及其他國別或區(qū)域的文學研究�����。志同道合的學者在一個研究室長期進行相關(guān)研究��,相互磨礪���、相互啟發(fā)、相互拓展����,一定會有巨大的成效�。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當前外國文學學科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是什么��?
程?��。夯谖覀€人的觀察,一方面是外國文學學科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外國文學學科的危機。語言文學在激發(fā)一國之民的想象����、磨礪其敏感性、深厚其情感和美感����、為其提供人生意義、形成和維護國家統(tǒng)一以及身份認同�����、輸出話語和價值��、增強文化領(lǐng)導權(quán)等方面�����,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被認為是一國文化的精粹���。此外���,文學不僅提供了一套話語,還不斷激發(fā)著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西方之崛起不僅依靠其科學技術(shù)���、工商業(yè)和軍事��,更依靠語言���、文學、哲學��、歷史對共同體靈魂的建構(gòu)和塑造��。19世紀60年代,英國教育家和批評家馬修·阿諾德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tài)》中批評英國人偏重于工商業(yè)�,只追求強大,而忽視了文化�����,而文化才能使一國變得偉大����。他提醒英國人:“假若明天英國被海水淹沒,那一百年后����,這兩者(指工商業(yè)和文化),誰更能激發(fā)后人對英國的愛���、興趣和欽佩����?”
正因為一國的語言文學如此重要�,一個有志于成為全球大國或維持全球大國地位的國家,一定會一方面強化本國的語言文學����,另一方面����,在對外研究中�,把外國語言文學作為重中之重���。學習和研究外國語言文學����,不僅可以豐富本國的語言文學���,也是深入了解外國情形和形成“國際視野”的關(guān)鍵渠道���。
事實證明,一國對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是其自身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方面��。當前�����,我國正處在向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邁進的關(guān)鍵過程中�,對外研究比此前任何時期都更為重要,也比此前任何時期都更有條件��。中國的復興之路急需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的大力支持����,中國的外國文學學科也有待進一步發(fā)展壯大。但不無憂慮的是����,走遍全國高校的外國語言文學院系,試問大學生中還有多少人在堅持文學研究并將其作為畢生事業(yè)�?
開展全球史視野下的外國文學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有哪些研究方法或理論對外國文學學科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程巍:改革開放之初�,一方面出于對當時文學政治化的反感,一方面缺乏對歐美文學理論的全面了解����,我們引入了美國文學理論家勒雷·韋勒克的“內(nèi)部研究方法”,將這種似乎“去政治化”而關(guān)注于文學內(nèi)部形式本身的文學理論作為當時中國文藝學重建的基石�����,乃至文學學科的合法性基礎(chǔ)。而我們所不知的是��,形成于冷戰(zhàn)之初麥卡錫主義時期的韋勒克的“內(nèi)部研究方法”本身就是美國中西部重農(nóng)主義�����、右派保守主義的一種文學意識形態(tài)����。根據(j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一般說法�,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tài)���,其特殊性正在于形式��。那么����,“內(nèi)部研究方法”的引入并沒有在文學研究中“去意識形態(tài)”��,而是以一種意識形態(tài)替換了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
我并不是說改革開放以來,引入的文學理論只有韋勒克的“內(nèi)部研究”�����。相反���,西方古今的文學理論����,尤其是現(xiàn)當代的文學理論在中國遍地開花�����。但在學科合法性上�����,它們被“內(nèi)部研究”貶低為“外在研究”�����,不是文學學科的“正宗”��。但這些“邊緣”理論對三四十年來一直處于霸權(quán)地位的“內(nèi)部研究方法”形成了挑戰(zhàn)����,文學研究空間大大拓展�,研究層面更為豐富和復雜���,這也是2013年國務院學位辦頒布外國文學學科新的五大方向的原因����。
不過���,我一直有一種觀點,就是我們并沒有完成“文化去殖化”的過程���。而缺少這一過程�����,我們就受制于許多幽靈��,我們的研究就有可能落入陰魂不散的西方文化殖民主義的歷史認知窠臼�����。但更多的時候��,這種文化殖民化是自我施加的��,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再生產(chǎn)——它產(chǎn)生了一種民族自我憎恨�����。文化殖民化的一個后果是癱瘓了我們自己的文化創(chuàng)造力��,但“文化去殖化”不是走向自我封閉�����,而是通過“去蔽”���,通過“驅(qū)趕幽靈”�����,獲得一種更加健康����、開放�����、自信的態(tài)度。
新時代提出的“兩個結(jié)合”對文學研究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推動了中國文學研究與外國文學研究突破當初的學科藩籬,走向彼此���,催生出一種“中外文學關(guān)系史”的全球史追求���。這是一個大有可為的領(lǐng)域,不僅能打破此前的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歷史敘事模式���,而且能夠形成一種十分有利的“交叉的目光”�。在當前的學術(shù)探索中��,我們面臨的首要任務是����,重新審視并調(diào)整整個學科的知識體系����,以確保其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學術(shù)環(huán)境和研究需求。
《中國社會科學報》:外國文學研究領(lǐng)域的國際合作與交流日益頻繁�����,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shù)界的聲音也越來越響亮。外國文學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您如何看待外國文學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意義?
程?����。航涣鞯念l繁程度���,并不等于交流的深度�����。文學研究比拼的是語言和政治的雙重敏感性�����,此外�,它還廣泛涉及其他學科����,并且涉及想象力——文學想象力、歷史想象力和社會學想象力�����。
不過,“外國學者”的身份也是一種優(yōu)勢�����,即具有一種不同的批評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和認知方式����,可以獨辟蹊徑,對外國文學有一番本國學者未曾預料到的解讀�。這就像西方的女性學者、左派學者和前殖民地學者對所謂“白種—中產(chǎn)—男性”文學的解讀��,因為他們所處“位置”不同�����,自然別有洞天�。如果一個外國學者失去自己的主體性或者說外在性����,而趨同于自己研究的對象國的文學觀念和方法�,那么�,他的角色便會退化為一種模糊的回響,僅僅重復他人的聲音�����,失去了原創(chuàng)性和個人見解的獨特貢獻�����。
文學在跨文化交流中從來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學具有一種特殊的不見行跡的滲透力量���。但與一國的政治和經(jīng)濟的國際地位不同,一些小國(如拉丁美洲國家)也能夠成為文學大國���,影響其他大國����,而所謂政治、經(jīng)濟大國則可能是文學小國��。
此外����,正如俄蘇形式主義者所說,“文學性”產(chǎn)生于對日常語言的系統(tǒng)偏離���,而外國文學相對于本國文學來說更是一種“陌生化”�,這就為外國文學的接受創(chuàng)造了條件����。在跨文化交流中,外國文學有利于本國文學的更新和豐富�����;但也需要警惕����,文學所攜帶的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也在跨文化交流中隨著文學閱讀而滲入意識乃至無意識。外國文學工作者日夕糾纏在兩種語言中���,受著語言的磨礪,應該更具備一種語言敏感性,而語言敏感性與政治敏感性互為表里�。外國文學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意義,正如辜鴻銘當初所說的“拓展”���,而不是反彈回來變成一種自我封閉��。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外國文學學科的未來有哪些期待��?
程?����。合M芮袑嵉亍耙哉Z言���、文學為主體,向翻譯學����,國別與區(qū)域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領(lǐng)域拓展”����。實際上,外國文學研究從學科性質(zhì)上說就是多學科研究����,即以每一次特定的“問題”為中心�����,臨時組合相關(guān)的學科��。這意味著不存在一個固定的“多學科”“交叉學科”研究領(lǐng)域�����。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聯(lián)系的世界觀也是一種方法論�����。我認為��,或者說期待�,外國文學學科將從零碎的孤立的研究漸漸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聯(lián)系的整體����,也就是說,在全球史的歷史進程的全部復雜關(guān)系中研究文學����。這樣����,才能充分體現(xiàn)文學研究的價值�����。